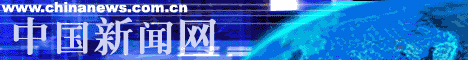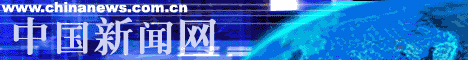周培源教授是蜚声海内外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科技界的卓越领导人之一,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捍卫世界和平作出杰出贡献的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促进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人民外交家,也是一位大力推进科学技术普及的热心倡导者。
生前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国科学家中最早担任国际理论与应用力学联合会的理事、国际科学家联合会理事及出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全体大会的中国代表和首席代表,并于1962年当选为世界科协副主席。1980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80年和1985年两次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具有卓越贡献的校友”奖。
周培源1902年8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1993年11月24日在北京溘然长逝,享年91岁,是一位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世纪老人。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
周培源中学时代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因参加“五四”运动,触怒了校方,被学校开除。后来,他考上了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的插班生就读,一面开始涉足科学研究,撰写了一篇关于三等分角的数学论文;一面积极参与学校实施的“强迫运动”,多次获得了中距离赛跑的冠军。这两方面的锻炼都使他受益终生。1924年秋,他以优异成绩毕业,被送往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系二年级学习。1926年春获学士学位,同年秋获硕士学位。
1927年春,周培源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研究生,做相对论方面的研究,于1928年春获理学博士学位,并获得了该校的最高荣誉奖。随后,他到美国东部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作短期访问学习,并经巴黎去意大利参加了一次国际数学学术会议。同年10月,他从意大利来到德国莱比锡大学,师从量子力学创始人海森堡教授研究量子力学,半年后因海森堡教授去美国讲学,他又应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泡利教授之邀,到瑞士跟随泡利教授继续从事量子力学研究。
1929年秋,周培源应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罗家伦之聘,从瑞士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年仅27岁。那时的清华大学只有一百来名教授,其中有三位30岁上下的青年教授,他们的学识才华,风度气质,深受同学们的爱慕与敬仰,被谐称为清华“三剑客”。周培源就是其中之一,他主讲理论力学和相对论等理论物理课程。由于课讲得生动有趣,富有深度和逻辑性,出题和解题思路也非常之妙,常能把人带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以致半个世纪之后,他的一些学生还能清楚地记得他的第一堂课,第一次考试和第一次听他的学术报告的生动情景。
1936年,他利用年休再次赴美,到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从事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其间,他参加了爱因斯坦教授亲自领导的广义相对论研讨班,并登门拜访了这位科学大师,还结识了他的得力助手英斐尔德等一些朋友。
1938年5月4日,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开学。西南联大的校舍在城西北,周教授的住处却在城外西南郊的一个小山村里,陆路相距19公里,走水路则要三个半小时。他就买了一匹马,每逢上课,他五点多钟就得起床喂马,刷马,备鞍,送两个女儿上学,然后再骑马赶到学校上课。被戏称为“周将军”。一次马被车惊,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一只脚挂在脚蹬子上,被拖着跑了长长一段路,幸遇一位农民把马拦住,才幸免于难。还有一次,因学校有事,回家时天已很黑,马迷失了路,连人带马摔到一条沟里。就是这样,他也风雨无阻,按时到校上课。
抗战期间,一心想以科学救国的周培源,放下了不能直接为抗战服务的相对论,毅然转向了应用价值较大的流体力学难题:湍流理论的研究。1940年,他写出了第一篇论述湍流的论文,发表于该年的《物理学报》上。也就是这篇文章奠定了湍流模式理论的基础,是他一生中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之一。
1941年,周培源利用第二次休假机会带领全家赴美,参加美国组织的战时科学研究。他先在加州理工学院继续研究湍流。在改进、完善1940年工作的基础上,于1945年在美国《应用数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脉动方程的解》的论文,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行家们的注意。湍流模式理论也由此而生,人们至今仍在引用此文。
由于他在湍流理论上做出了卓越成就,美国政府邀请他参加美国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的科研工作,做鱼雷空投入水的项目,终于使他有了以科学为武器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的舞台。二战结束后,该局解散,周培源被留下写总结报告。这个报告后来被美国海军部划为保密文件,直到1957年才解密。美国海军部还很快成立了一个海军军工实验站,继续从事军工研究,并希望周培源参加。但要求外籍人员必须加入美国国籍。周培源考虑当时赴美参加反战科研工作,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现在二战已经结束,没有必要再留在美国,就婉言谢绝。这是他第二次拒绝加入美籍。
1946年6月,周培源代表中国中央研究院参加英国皇家学会举办的纪念牛顿诞辰300周年纪念会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9月去法国参加国际应用力学大会,在会上做了学术报告,并当选为理事。同时,当选为新成立的国际理论和应用力学联合会的理事。10月回到美国。这时,国内的战事又起,他的一些亲朋好友都劝他不要回国,他不愿把自己的生命之树定植异国他乡,毅然于1947年2月,与夫人携三个女儿,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多灾多难的祖国,继续在清华大学任教。
一年以后,他再次应邀赴英国参加国际应用力学大会。由于国民党政府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理事会开会和会议宴请时,会议主席把他的座次排到最后和倒数第二,使他深深感到,即使作为一名科学家,在他从事国际科学交流活动的背后,也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做后盾。
1948年11月7日,周培源从英国回到北平。1949年,北平解放后,周培源先后出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和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承担了大量的学校领导工作和教务工作,到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离开清华到了北大。
周培源从1929年学成归国,到1993年逝世,对我国科学教育事业、和平外交事业与社会进步事业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他是一位勤奋的、严谨的、锲而不舍的、敢于坚持真理的、成就卓著的科学家。
周培源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为物理学基础理论的两个重要方面,即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论和流体力学中的湍流理论的研究。
在广义相对论方面,他一直致力于求解引力场方程的确定解,并应用于宇宙论的研究。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就求得了轴对称静态引力场的若干解,与静止场不同类型的严格解,并于1939年证实,在球对称膨胀宇宙中,若物质和辐射处于热平衡态,则宇宙必为弗里德曼宇宙。70年代末,他又把严格的谐和条件作为一个物理条件添加进引力场方程,求得一系列静态解、稳态解及宇宙解。还指导研究生进行了与地面平行和垂直的光速比较实验,以探求史瓦西解和郎曲斯解哪一个更符合静态球对称引力场的客观实际。初步结果已显示出,郎曲斯解与实际相符。
在湍流理论方面,是他最早在国际上首先提出脉动方程,并建立了普通湍流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对若干流动问题做了具体计算,结果与实验符合得很好。1945年,他在美国的《应用数学季刊》上,发表了题为《关于速度关联和湍流涨落方程的解》的论文,提出了两种求解湍流运动的方法,立即在国际上引起广泛注意,被多次引用,进而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湍流模式理论”流派。
50年代,他利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轴对称涡旋模型作为湍流元的物理图像来说明均匀各向同性的湍流运动,并根据对均匀各向同性的湍流运动的研究,分别求得在湍流衰变后期和初期的二元速度的关联函数、三元速度关联函数。之后,他又进一步用“准相似性”概念将衰变初期和后期的相似条件统一为一个确定解的物理条件,并为实验所证实。从而在国际上第一次由实验确定了从衰变初期到后期的湍流衰变规律和微尺度扩散规律的理论结果。80年代,他又将这些结果推广到有剪切应力的普通湍流运动中去,并引进新的逼近求解方法,以平面湍射流作例子,求得平均运动方程与脉动方程的联立解,就这样,经过半个世纪不懈努力,“他的理论一步步得到完善。如今,这位国际公认的湍流模式理论奠基人—周培源—的理论体系已相当完整,从各相同性的均匀流到剪切流动,从射流到尾涡……都可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下得到解释。今天,我们虽不能说湍流问题已完全解决,但可以说,周老的理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完整的湍流理论。”
二、他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助人为乐的、一身正气的、远见卓识的、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60多年来,周培源一直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他不仅在传授知识、组织教学、创建专业、指导科研以及发现和培养人才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还积累了丰富的教学和办学经验,形成了自己的教书育人风格和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其中最突出的是以他自己的学识、见解和治学、做人之道等人格魅力,感染着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
他讲课非常认真、起劲,说话也快,富有感染力,而且十分注意启发诱导学生去开动脑筋。一位50多年前听过他的课的院士说:第一次听周老讲理论力学课时,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们从未思考过的问题:牛顿的三大定律可不可以归结为两大定律?这一下把我们都难住了。然后,他一步步向我们解释牛顿力学并不是孤立的没有内在联系的三大定律,一切物理理论都有它的内在逻辑。正是这第一课激发起我对理论物理学的浓厚兴趣。他的又一位学生说,周先生经过多年积累,收集了各式各样的力学难题,有时就以这些难题作为习题或考题,让同学们做,目的在于训练学生的思维方法,让同学们明白,在探索某一问题的科学解答时,首先要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思想方法。否则你就会陷入误区。还有的学生说,周老是一位很严肃的学者,但也很有风趣,有时讲课就像讲故事,让你听得入神,并鼓励、启发学生提出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更为可贵的是,周老教了一辈子书,有些课程内容已熟得可以“倒背”出来,但每次讲课他都认真备课,写出新的讲课提纲。
他的几位当年学生和助手都说,周老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基本训练,培养他们分析问题的能力,提出自己看法的能力,明辨科学是非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他经常强调“学生的基础打不好,以后就别提了。”并说,“读书不能满足读懂,而要能会用,才算掌握,力学尤其如此。单做习题是不够的。应该接触实际,学习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他还特地把一位大学刚毕业即将走上科研岗位的学生,约到自己的书房里,郑重其事地向他提出了三条建议:“第一,在毕业后的一年内,要把过去所学的主要课程,不管对现在科研工作有没有用都复习一遍,有些可能你从事的专业永远也用不上,但这些课程中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和技巧,很可能对你今后的工作会有重要启发。这些都是基础,基础不牢就盖不了高楼。毕业后不抓紧复习巩固一下,过几年就会忘光了,到时候再补不如现在巩固效果好。第二,搞科研像打仗一样,开始实力不够,不能搞全线出击,一定要重点突破,抓住一点深入下去。科研不同于教书。是创造性工作,千万不能搞万金油,样样通样样不精是不行的。第三,科研工作是十分艰苦的,一定要勤奋。我这个人就很笨,但我勤奋,要以勤补拙。”周老的这些至理名言,是他多年科研实践的总结,他的许多学生按他的教诲去做,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更多的学生至今都还清楚地记得,周老如何指导他们的阅读论文,如何指导他们选定论文题目,如何指导他们进行科学实验,如何指导他们撰写论文,以及如何逐段逐句的帮他们修改论文的感人情景。一位他中年时期的学生说,周老一再向我们指出:“阅读论文一定要分清主次,必须先看几篇主要文章,掌握文章的基本思路和学科的发展方向,千万不可漫无边际地乱看一气。对论文中涉及的许多次要问题只能暂时放一下,以后再逐步加深理解。”一位他老年时期的学生说,“在论文的选题上,周老强调难度、价值和可行性三者的结合,重视学生专业特长与论文内容的结合,在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给予宏观把握。在论文进行的过程中,他经常询问论文的进展情况,遇到哪些困难,应采取什么相应的对策。”他的另一位80年代的博士研究生说,“周老对影响实验精度的关键因素十分注意,每一次找我们谈话,总要我在比较高的精度上说出它对实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依据是什么,不准用‘差不多’这个词回答。”“他还告诫过我,‘做实验不要光同外国人比仪器,要比想法。仪器的先进程度,我们比不过,但想法我们能比过,中国人很聪明。’对实验和理论推导中的计算草稿,周老也有严格要求,不少学生曾为此受过批评。在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他的许多学生都养成了及时誊清计算草稿,不随便乱丢计算草稿的好习惯。这给他们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很多方便。对研究生们的毕业论文和提交学术会议的论文,周老师更是严格把关。每当学生们的学位论文手稿交到他的手中后,他不仅逐段逐句斟酌,反复修改,而且亲手推导验证有关公式,对标点符号、图注、目录和页码都仔细校核。他青年时期和耄耋之年的研究生都说,“在我撰写的博士论文及发表的有关论文中,浸透着周老的心血。每一篇论文的完成及其英文表达,无不经周老数次悉心修改。”一位研究生提交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英文摘要,经周老审阅后,“密密麻麻地改了几十处,除了新添的内容外,所有的语法、单词拼写和标点符号的错误都不放过,并让我按修改后的稿子重新打印好再送他看。如此折腾几次,他才放行。当我将这两页密密麻麻改过的原稿拿回宿舍让其他同学看后,他们无不感慨地说:‘周老这么大年纪了还这样认真,实在难得。’”
此外,他还是一位献身于世界和平事业并作出杰出贡献的老战士,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是一位活跃在世界科教舞台,为促进国内外的科教交流与合作及科学技术在我国的大普及作出杰出贡献的我国科技界的卓越领导人。这两方面的事迹,本文因限于篇幅从略。(摘自《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