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ʷ����� �������������
 ���뻥��(0)
���뻥��(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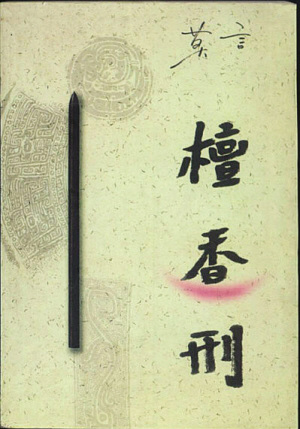
������̴���̡���һ�������Գ�������ȥ̸�۵���Ʒ������д�����ǹ��£�����������ѧ�������涨�͵Ļ�е����������ս�����仰˵�����������мȳ�������Ϊ���е���ѧд������ȥ����������ͬʱҲ�ܳ����Ѿ��൱ŷ�����ȷ溺������ִ���У����˵��������ѧ�Ĵ�ͳд������ע�����ʵĻ�����ô�����ȷ�֮���Ѿ������ʴ�Ѽ������ˣ������ظ�������ƶ����Լ���ȷ���ٵ���Ҫԭ���ظ��Ĺ��£����Ƶ���ʷ����ͬ���龰�����͵��������ã������DZ�����Լ����������ʶ����˼����������20���͵����۷�չ���ҵ����Թ����λ�ã���ѧƶ����ֻ���ֹ������ͳ��д����˵��Ʒ�������ң��Ѿ�û������֮ϲ��ֻ���ٶ���֤��֤ʵ����Щ���ۻ�˻�ˣ��ܻ���ijһ��������߶����ص����ǣ����ܹ�һ����Ҳ������������ִ����浽���۷壬�������¡���������ʱ�����Ҳ��������Ĵ����Ŀ��ܣ���������ĩ��Ҳ�������ۼ�Ҳƣ���ˣ�һ�ж�������֮������ź�Ƿ���Ѿ���ȥ�������ϻ����б��������������Ծ���
������̴���̡�����������һ����ѧʱ���ע������������ˣ����Ĵ��ڳ�����ѳɶ��ֵ�д����ʽ����ѧ��Χ���ο�������һ���ľ߱�������������ϵ��ƻ��У���Ȼ�������߶��ԣ�ȷ��һ�ֶ��������ϵ���ؽ����������м��ʼ�յ�������ԣ��������������Ľ����ߣ������г���������èǻ�����ܽ���Ի͵ĵ�����������ĸ�硢����˹�İ���̨ͬ�ݳ�һ�����ҵ��ⲿС˵Ҳ������ܱ��Ӱ��������ա�������ѩ�Ķ������͡�����èǻֻ���ڹ㳡��Ϊ�Ϳ�����ݳ�һ�����ҵ��ⲿС˵Ҳֻ�ܱ�������Ļ��ֱȽ���̬�ȵĶ����Ķ��������Ī�Զ���һ�����Եľܾ�������Լ�ѡ�������Ե�����������һ��ģ����������Լ��������ġ�Ϸ�ġ����Ĵ���ʹ�ã������ر��Լ���Ϸ�绯Ч����ע�أ�����˵��������������dz�ԡ����š����������£���̹���ڸ���д����������С˵���������˵�������ļ̳У�����ʵ�Ѿ����˻���γ����˼����Ȼ����ôֱ��˵����ȴҲ�Ӱ�������������ͬ������ѧ����IJ�����Ȼ������˲�����ʦ�����͵��ع۲������������˵ľ���������Լ��������ڿ�����ȼ�������ŵĵ����ﶼ�ܱ����Լ���ʵ��̬�ȣ���ȻҲ��Щ����������Σ����ڵ����ϴӲ�ʧ��ʵ��������Ҳ������Լ���ȫ�����¶�������������������ǿ�����Ե���Ϯ�ľ��裬�������Եġ���������Ī��ѡ���ˣ��������ȥ������ʱ���ˡ��ص���䡱����Ϊ����ѡ�������Ծ��ڡ���С˵����ԭ�����������ս����س�Ϊ����������ԵĽ��죬�ڶ�������ѧ�Ľ��ѹ���˶������ѧ�ļ̳еĽ��죬��̴���̡������һ������ʱ�е��顱�� ������̳������˭���������������Ժ����������ͬʱ�ܾ��أ��ο����ܾ��Ļ���ʱ�еġ����족��
������֮��������д��Ī�Խ������ʷ�ķ�ʽ�Ƕ��صġ���֧�������ԽΪ���µ��ִ���д���У��㲻�ܲ��շ��ڡ�̴���̡������µ���������������ֵ����д��һ����С����²������ӣ�����¿���Ů���˹�ü��Ϊ���ģ���������������èǻ����ɿ�����ʿ����������Ĺ������������̲�˾ִ�̵Ĺ������Լף����ĸɵ����������й�����֮�ĸ���֪��Ǯ�����Լ������ɷ����������ݳ��ֵ���С�ס�����ǣ�����Ϊ��ִ�̣�Ů�����������ᣬŮ�������Dz����֤������Ů�����϶�ͷ̨��Ů���ɷ��ǹ��������֣���������ĥΪ���£�Ů����������ȴ��Ī��������ڴ��ۣ�������ᣬ�߳���������������ö����Ķ��������ǣ���Ϸδ������Ļ��������С˵����ͷ�����Գ�������4λ���˹���������ʽ������Ҫչ���ľ��飬�����Ը������ϵһ���������������Ը�������������ɫ��Ϊ�����Dz������¼�չ�����µ�λ������˵Ϊ���������˹���������Լ���ĩһϵ����Ǯ�۷ɡ���̷��ͬ����������������֮ǰ�����Ĺǵ�����ij����������������˴�̨���������֣����Dzп�����Ӳһͬ���������رܣ�ֱ��һ�������̶��գ�����β�����������˵Ϸ�����ͷ4λ���˹���˵���ɶ�Ӧ����ɫ�˵��ڴ�����Ϊ���ࡪ����Ѫ���Լף�������ü����������������ΪŰ��С�ף�����������֪�أ��������⣬����������һ��С���ȴ�����һ���峯�ı������������ˣ�����ְҵ�����۱�ɱ��ɱ�ֻ�ɱ�ˣ����������˵IJ������������Ļ��𣬴��ý��㣬ĩ��ͼ���У�ֻ�Dz�ͬ��ѳ�����ˡ�
����Ī��֮������ʷ�����Ѿã������������ʼ��֮��ȥ����ʷ����ڴ˵õ������쾡�µķ��ӡ����ǶԽ���ʷ�Ľ�������Ϊ��̴���̡�д���˸����Ķ������Ǹ����⣬�Ǿ���³Ѹ�������ֵģ�������ū�ţ���������ɫ�ı任���dz�Ϸ�ĸ������Ǹ���Ȼ�ԡ�������һ���ǣ�Ī��д����ʩŰ�Ŀ������Ű�Ŀ�У��������Լ�ʩŰ�����������������ĸ�Ը��������ɽ���֮�䣬���Ķ���������˼��Ҳ������ǹ�����ԣ���ʶ�е�����ʶ������������Σ��������У������ѵ���������ҩ���Σ�������������Ī�Դ����ᵽ��Ѫ�ȡ���Ѫ�ȣ��뽭ɽ����ʷ֮���ֹ���������ʱ�չؽ��ɱ¾�ĵ�ɫ��Ϊ��ʱ��ע���������˸����ӣ��ھ����¼����ҳ���ʷ������������������ʽ��з���������֪�Ŀ��ʣ���һ�����ң��ṩ�����˵ġ��������ڴ������ȷ�֮����һ������·��Ѱ��һ���й��ִ�����д���Ļ��﷽ʽ������Ҫ�Ķ�����
����(������ ����ϵ�й���Эȫί��ίԱ���й���Э���в������Σ��ڰ˽�é����ѧ����ί��)
>������ţ�
>�Ļ����ž�ѡ��
- ��������ĵ��ͤ������������ �����������Ļ�������ײ
- ��̽�á�����˹���������Ļ��Ų������� �ػ������ǻ�
- ���Դ������ѧ�ӽ�̽�������й�Ů�������Ǩ
- ��Ư������ġ��������������Ѿ��糪��������
- ��˫���������ڲ�ͬ�����������ϡ�����ʡ�
- �����𡢷�ϵ������...������������Ļ�����
- ���ʹ��Ƴ�����ѩ�����Ϲ� ���ѣ�����ֱ���������ŷ�
- ����ʮ����Ƶ��Ļ�������̳��ѧ����ʫ�轲���ҹ��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