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ѧ���磺���Ե���������
 ���뻥��(0)
���뻥��(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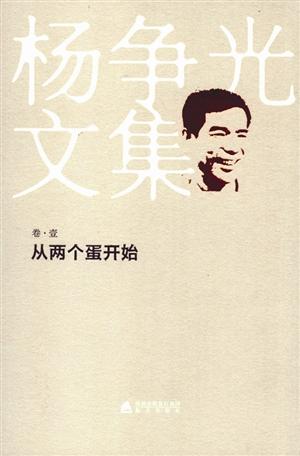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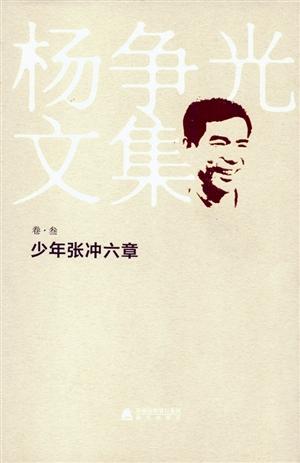
�����������������ʮ�������������ļ���
���������߰�
����11��28�գ��ɺ�������羫�ı༭�����ʮ�������������ļ�����ʽ���淢�С���Ϊ����������������Ʒ���״�ȫ��Ἧ�����ļ��ij�����������ѧҲ���й���̳����Ҫ�ջ����ڳ���ʷ�ϵ�һ�α�־�Դ��¼������쿯���ı������ߵ�ר�����£���5���ؼ��ʵ��������������ѧ���硣
����A.
����������
���������Ǽ�Ϊ��ͨ�������ƺ����κ������¶������棬���ܷ�λ���ʣ��������������˸ߴ��Ӳ���Թ���ϴ�ӹ�Ч�⣬����������ò����Ծ���ͻ����
��������ʱ������������ʮ�����ʫ��ij��ԣ�������������ʫ��ҿ������ڶ��������������ٽ���ľ���˻��������ֻ�����������Ϊ��ӳ�ı��������磬��д�����֣�д����������������ľ�������ѱ����˳ɴ�ĸ�������Ǿ����ij�����֡������д��������ڡ������Ҫ�����ǿù¶���������У����ǡ���Զ�������ģ����������Կ���ζ��ʫ�еġ���������Ǹ���������ġ����������ͬ������������ֺ�������Ĺ�ϵ���������أ���������
������Ϊ����������Ѱ�����������Ե�����������������Ʒ�С���ʫ�衶��վ�ڱ����Ľֵ����ˡ������ͷ�������������˹���ı�ʶ�Է��ţ���������������㣬Ҳ�����������յ㡣ʫ�С��������¡���С�������ĸ����������������Ȼ�Ѿ��߳�ȥ������Ҳ����ص�С���ˣ�����Ҫ�ڴ�ط������ͬʱ�������Ĺ����������յı������������ߵ�ʱ���������˵\���˴�ط������������ϼ�\�ܲ�����ߵ�����\�ͻ�����ׯ�ڡ�����
���������������ʫ����1984��ġ�ʫ�����ϣ�1997�꣬�������ڵ�һ�μ��������⣬�ŷ��������С˵��Ӱ����������ͬʱ�Ǹ�ʫ�����ߡ���ʱ������Ȼ��ũ��ʽװ������Ϊ�����ݳ���һ�������Եúܿ�����������ɫ�ľ��̲������������ϴ����ҹɫ�������ʱ�ᱻ�紵�������뵽�����������þ�������ƣ������ǿ�����ӡ������ڵ�ij�ξۻ��ϣ������������������ʶ���ʫ��ʱ����ʮ���꣬����һ�α�ʫ�е������������翴���Ǹ�վ�ڱ�����ͷĬĬ��������꣬����С������ʫ�ˣ�Ҳ���������Եײ���ˡ�
����2006����ҵ��������ϼ�̽�ã������������µ������������������Ѵ������ӣ������������Ľ��ۣ�����ϸ�鿴״����ë�İ���ɫҶƬ�����������б˴˾���������ܶ��������ƺ�ʲô��������������ԣ�ǡ�ǿ���ȥ����ͨ��
����B.
�����ڷ羰
�������ڷ羰�����������һ���ж�ƪС˵���������������硶��ͽ�������ײ��̡����������ӡ��ȶ���ڴˡ�1993�����죬��������ɳ��ͷ�ֱߵ�һ��С���żȻ�����Ȿ�顣
������������ͣ�磬С����������յú���ơ���վ�����һ�ǣ�һ���������˾��Ķ�ƪ����ͽ�����ɡ���������Ȼһ�������������ڭ���³Ѹ�����ܵ�ij�־�Υ���Ķ���С��������Ǹ��±�ɽ�����ũ�����ľ��������������Ц�Էǣ�������̴���ͣ��ƨ�ɵ���ä�Գ�������ǰ���µġ��ϸ�����������峤Ҫ������Ϊ˵���䡰�ϸ������ʸ��߹��ォ�����Ѿõ�һ�Ż�ֽ�ó���֤�����������û�б�֤���ɡ��ϸ����������������Ǹ�������ͽ����ù�������ɴ���û�õ���������ٽҷ�������˯Ů�˲�����Ʊ�ȳ��š�С˵���Լ�Ϊ���أ���������������������࣬��ʫ����Ĭ�������������еĵ�������ǣ�������һ���������Ͱ�����ij����������Ժö��Գ��������硰���������ɣ�����ˮ����ʯͷ�ϵ���������ֱ�һ����������ʱ��̫�����ʻ���е�̫������ëë��һ�����������̫꣬�������������ʱ��Ҳ����ֱ�һ������
����1996�꣬�����˻���Զ�С��ǵ�ȥʱ���г��϶�������-����Ү�ġ�������ղķ˹������˹�ġ�һ�����������ҵ�Ф����;�У���������ڹ��졢���˶������ġ��ڷ羰����̹�ʵ�˵������λŷ���ִ�С˵��ʦ��ȣ��Ҹ�ϲ���������������С˵�����������ĸ��й�����������ͬʱҲ�������������˾���
����C.
����˫����
��������һ�������С���������û��ע�⣬���ſڶ��ഫ������ʢ��������Ϊ�й���������Ӱ�������ɵĴ����ʡ���Ϊ���˶���һ�ĵġ�˫���͡����ż���̼������ˡ������ſ�ջ��������а���������������˺����������ҵ���������Ƭ���ȳ���������һ����������ӹ����̸��˭��д��������С˵ʱ������ȷ�����˶Ը�Ƭ�����������Ƴ硣
������˫���͡���Ʒ��1990�꣬������Ҵӵ��������Ƭ�������ٶף���������ܶ���д���ܶ��֮�⣬�ұ��ⲿ�ۻ������ӰƬ������������ͬããɳ����ײ��һ����ɣ�������ʻ�Ѥ�ã�����Ⱥ������Ϊ֮һ��
����������Į���˫���Ƴ������������죬�����������û�����У�ɱ�˲�գ�۵ġ�һ���ɡ��ü�ʮ������ŷ�ɥ����С���ͺ����������ϣ�Ѱ�ұ�����ָ��Ϊ���Сϱ�����ã���������һ���ɡ�����Ҫ�Ժ���ʩ�����������������ˡ����ǣ�һ��ɱ��֮�������������һ���ɡ�����Ҫ�����𣬡������������˺���һ��Ȣ��Ǯ��ȴ����ɳ�������ۻ𡣱�ˮһս�ĺ��磬ֻ���Լ���ȫ�Լ���
��������һ���ľ߶���������й����ɵġ�����Ƭ�������Ź�����Ӱ������Ʒ�ʡ�����˵�̣���ɿ�飬������ۣ�����ʮ�㡣������ڼ�Լ��������Ϊ������ȴɢ����ḻ�ں���ӰƬֻ��С���������조�塱�ֵġ��������������ν����������������塢Ӣ�۵ĸ������˾���ڹ�͡���ʫ�黭�⣬����ʤ�࣬��������Ͷ�ʹ��ڵ���ν�������ƣ���û�ܴﵽ��Ƭ��ˮ��
����D.
�������Դ�
�����������ⳣ�õ��������һö���š����Դ峤�������ĵ��������ǡ��������ӡ���ƴ������ʵ�ϣ��������ǡ��峤���͡����ӡ������������ׯ�ĵ����ߡ�
������������������Ǭ�ض�����С�壬��ƪС˵������������ʼ���������¡����룬��ʱ�����顢��ѧ���飬���С����븣���ɵ�����������Լ���������أ�������˹�ĸ��ױ��ǵ������࣬�Լ�Ī�ԵĶ���������һ������Ϊ��ѧ������һ��������ȥ�ķ羰��
��������������û��������Ұ�ģ����������Լ�����ѧ�龳��������ϲ����˼���룬ϲ�����̡����ĺͳ�������һ����ȫƾ���¡����ڷ��Դ壬����1997���һ�μ�����ʱ������˵��������������ĵ�˵Ҫд����һ����ƪС˵��ͨ�������С�����д��չ�ְ�������͵�ũ���Ǩ��2003�����������������ʼ���ڡ��ջ���־��ճ�������һ��ҫ�۵����磬��������ƣ�ֵ���̳�����������������˷����Ķ�֮�֡�����10�£�������ѧ����������˵��б������൱����һ��ʱ����Ķ���������Һͼ��˵�������¡���ʱ���һ���ûȥ�������������Դ����һ������Ȼ���أ���ʮ����������Щ�Ը�������Ů���ٷ�������������Ʈ�������ǵ����������ǵ������������������֣��Լ����ԳԺȺȡ����մ�����������Ȥ�¡������鶼�Ǵ����ճ����ҳ���̣��ʻ���֡��ڷ��Դ����д�У����������һ�����������Ļ������ݺ����أ����¹�������������Ȼ�������ȵ����־��䣬������ʮ�����й�ũ�����Ӱ��Ҳ�������й���������͵�����Ǩʷ����������Ҫʱ�ڵ���Ҫ�¼������������ҵ�����������������Զ��ӡ����
����2006��10��5�ջƻ裬�����������Դ��ԭ�͡����������������·�����Ž����ׯʱ���ҿ���·��������Ϥ���������������������ǻ�Ҷ������������Ϳռŵ�ƻ������ڵ��ƾ���שǽ�ϣ��ο����п����֡�����塱��������й����Ĵ�������û�ڼž�Ϧ�������ڣ����Ǹϵ�������Ĺʾӣ�����һ�������ŵ���Ժ�����淿�Ӿ�Ϊ�������������Ͱ�����ǽ���İ��Ĵ�����ǽ�Ϲ��ž���𣬴�̨��ɢ���ź��Ұ��С�Ļ����ӡ���������������ļ����������������ϣ��л����о��¡���Ϊ����ȫ�ڣ���û�м�������ķ��Դ��ˡ���ʵ��Ҳû��Ҫ������Ϊ���Ƕ���Զ�ʻ������������������ϡ�
���������ر�˵�����й���������������������ص���д��С˵ԭ���ġ���Ȥ���롰г�ʡ��ѳ���̳ϡȱ����Դ�������ܿɹ���ǣ�������������ʼ��������г������ģ�������������������ر�����Ȥ���顣��������Ϊ�����Ǽ̡���Q��������������ÿ���һ���й�С˵��
����E.
����Ҫ�й�
������д��ƪ���֣����뵽�ˡ��⡱��Ԣ�⡪���ϵ�˵��Ҫ�й⡣֮����ѡ����仰������Ϊ���뵽��������ڶ��ص���Ҫ��
�������й���̳������������Ǹ����ص������������������ü���Լ�����֣�������������ʤ�Ĺ��£������˾��и��������ķ���������ԣ������������ڽ������õ�������������ʱ������������Ĭ��Ȥ��ʫ����š���Щ��ǡǡ�����������������ѧ�����
������ܶ���������ȣ�������ϧ����𣬲����������ӳ�ƪС˵������������ʼ�����������ų����¡�����ƪС˵���ϵ���һ���������Լ���ƪС˵�������š��ȵȣ�������̳���ϵĽ��������ĺܶ�С˵������ó�һ�ζ��ǹ�Ŀ���������ġ������˶����������Ա��С��ϵ���һ��������
���������е���������Ȥ�ѵ����ܶೣ�˵��Ⱥã���������ΪȻ�����縰�硢���������εȵȣ�����������磬ȴ���ٽ�ӰԺ��������ʧȥ�˺ܶ���������Ļ��ᡣͬʱ���������ֵġ�����ʱ�ˡ���˵����ֱ��ֱȥ����������ͬ���Լ����۽������˾��롣��ˣ���Ȼ��Ʒ����һ����ȴһֱȱ��һ�������ơ�
��������άŵ�������֮����δ��ǧ����ѧ����¼�����ر�����˶ԡ����ݡ��Ŀ��أ��ͺս�����������ΰ������������ʱ������С˵��Ц�������������������Ϊ��֮Ц����˫���ԣ����ǻ����˷ܵģ�ͬʱҲ�dz�����Ц�ģ��ȷ��ֿ϶������������������Ҵ��������С˵��������ܵ����ѵõġ����ݡ��͡�˫���ԡ��Ŀ�֮Ц��
����Ҫ�С��⡱��
���� �� ��
>�Ļ����ž�ѡ��
- ��������ĵ��ͤ������������ �����������Ļ�������ײ
- ��̽�á�����˹���������Ļ��Ų������� �ػ������ǻ�
- ���Դ������ѧ�ӽ�̽�������й�Ů�������Ǩ
- ��Ư������ġ��������������Ѿ��糪��������
- ��˫���������ڲ�ͬ�����������ϡ�����ʡ�
- �����𡢷�ϵ������...������������Ļ�����
- ���ʹ��Ƴ�����ѩ�����Ϲ� ���ѣ�����ֱ���������ŷ�
- ����ʮ����Ƶ��Ļ�������̳��ѧ����ʫ�轲���ҹ��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