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á��������ԡ��������ߣ����ж�����δ������
 ���뻥��(0)
���뻥��(0)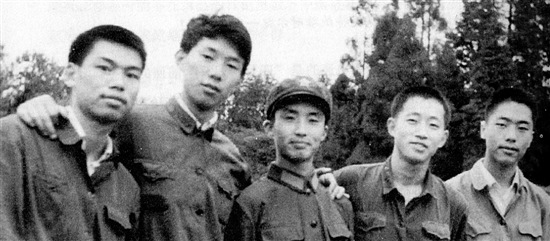
���������£�Ԭ������2009���Ƴ����ط�1976�������������ġ��������ԡ�����һ�顣2011�꣬�����ɷ�������ٰ棬�����ijɡ��й���������һ�ꡪ��1976�롰�������ԡ���ʼĩ����
����Ԭ����ʾ,�Լ���д�ľ����Ǹ��˵���ʷ��ȴδ�����������ʷ���ֲ�����������µı߽ǿհס�����ͨ�˲����κ�Ŀ�ĵļ��䣬���ǹ�ͬ������������Ϊ�ָ���ʷ�������ò�ṩ����ʷ�ϼ�ֵ�ı�ī����
�����ź����ܺ����ж�һ���ط�1976
������Сƽ�����֪����д�Ȿ�飬��������ǿ�ҵ���Ȥ����Ҫ���������еġ��ط���һ�ʡ��ط�����ζ�����·��ء��ֳ�����һ���˵��ֳ�����д�Ȿ��ʱ���¼�����Ҫ���������ҡ����ڡ����ҽ��뵽�����д�����̵��У���������ֳ�������¥�������ݵȼ�֤�ˡ��������ԡ����ľɼ����ڣ��Ҷ������˵���������һ���ط�����Ӱ�������˸п����ǣ���ν���ֳ�����ͨ��˵�ġ������˷ǡ������������Ҳ�ǡ�
�������ԣ���͵����˿�ν��ͬ������һ����ʷ����ʵ�������ط�֮�ã���ʱ��Ķ��������Դ�Ŀ�ġ��ֳ��С�������Ľ���ʼ�ճ�����������
����Ԭ������Щ�꣬���������ԡ������������Ҳ������������ж������β�Σ���ȣ�����״��һֱ�ܲ��á������������ˤ���ˣ����ֲ���������еIJ���ֹɹ��۶ϣ������Ⱦ����֢������ת�Ƶ��β�����Ȼһ�δα����Ȼ����ˣ�������ȥ����ʱ����������ֲ��ɹǵ����ⶼ�����ˣ�Ҳ����˵���⼸���������ˡ�������״������������ᡣ
�������Һ͵�����һ���ط�1976�Ĺ����У��������ź��ľ��ǣ����ܺ����ж�һ���ط�����һֱ�ڴ����ж���һ��������վ������������һ���ٴ��ط�1976�����ܿ���˵���������ʵ���ࡣû�뵽����Ȼ�������Ƕ��𣬴Ҵ���ȥ��������һ���˵ļ����δ����ĽᣬҲ����������δ�Ƶ����ࡣ
������Сƽ�����Ȿ��Ĺ����У���Ҳ���룬�������ж�������һ���ط�����������һ���龰�������д���ֻ��������Ӱ�죿
�����ӳ�������ֿ�������һ�¡�����������1976���жԡ��������ԡ���������Ĺ����⣬����������һ�¼�ʱ��������д�����Ǵ����¼�����Χ�Ĵ���䣬Ȼ��Ź��ɵ�д��Ҫ�ĵ��������ж�����������һ˳��һ���������¼��ĺ��ġ�������ˣ�
����Ԭ�����������ϵ������������˽�̽�����������ԡ�������������ǰд�������������ߡ�������������ѧ��������������Ƕ���ɷ��永��Ա�����������ж����⣬���е����˶��ܾ��ɷá�
�����ҵĸ����Ϊ���������ԡ������İ�������˵�������Ļ�����20��������˭����Ҫ˵������顣���ܳ�ʱ����������һ�������Լ����������������ִ�̽ȫ�����Գ�Ĭ���ⲻ��һ����������飬����һ����Ҫ��ʷ�������˵��������������������������顣����Ҫд�ⲿ��壬��Լ��Ҫ�����˳Է���ϣ�������ܹ������ҵIJɷ�ʱ���永�����Ѿ����곤�߽�����������˵�������IJɷô���������ʷ����ζ�����ǶԱ��ڱε���ʷ�Ǹ��л�ԭ��������εġ�
�����ҵĻ��������ǣ�������Ϊ��Ҳ�ǵ����ˣ�������ʮ���Ժ�����������飬������ʱ��ij����������Һ����ǹ�ͬ�永�����ݣ��������Ǿ������ʺϵġ���ʱ��������Ҫ���永�������ڸ��ԵĹ�����λ�϶�������һ�����쵼ְ�����Ƕ���æ��Լ���Ǻܲ����ס��Ƚ϶��ԣ������ʱ����Ը�ԣ������Ը��˵�����У�������ڷ������˰�ǰҹ������ɱҲȷʵ���Ķ��ǣ���д����ʼ�ط�1976��Ҳ����Ȼ��Ȼ���¡�
������Сƽ��ij��������˵���Ȿ�������ڡ��ջ�������ʷ����Ŀ������ϵ�����µĽἯ��Ҳ��Ϊ�ˣ������½��↑ͷ�㶼�ᵽ��д���Ĺ��̣���ǰ�����Ĺ��£�ʹ��ͨƪ�к�ǿ�Ĵ���С�
�����ڶ��ߵĸо���������Dz���ֻ�������ڽ���һ�γ������ʷ�����ǵ�ӡ����ж�Ҳ����ı����������Ĺ��̡�
����Ԭ��������һ��ңԶ����ʷ����ʮ������������ʷ��ʲô��ʵ���壿�����������˳������������ݽ����֡����ԣ������롢�������ഺ��ǰ;����ȫ�������ǵ��겻ͬ�Ľ�������һ��Ǿ��ã������������ߵ�ʲôʱ������һ�־�����ب�Ų���ģ���һ����������ġ�������Ӧ��������ָ����ʲô����˵�ĺܶԣ������ڽ���һ�γ������ʷ������Ҳ��ͼ�ܹ�һ����ʷ����ʵ�������������˿��Իع˺ͷ�ʡ�������˿����˽��Ǹ�ʱ���������Ѫ���黳�����µĶ��߶������ʷ��ӡ����жϣ���ij��������˵ȷʵ����ı����������ĽǶȣ����ֽǶȵ�ѡ������Ϊ���������ı��ģ������ں��ġ�
�����Ҳ����ڽ����£�������д��ʷ
������Сƽ�����ڡ�Ѱ���ࡷһ���У������ж�ϰ���ڱ�����µı��������ĸп���ζ�����˵������ʷ�ϳ����кܶ����������Ϊ���˱�����¶�ʹ�����������������ġ��������ʱ������ƺ����������ӡ�ö���֮�ͱ����û�����ŵ����ࡣ����ʵ�ϣ��ܶ�����������ǹ��µĽ����н��н�Զ����û�������Ľ��������㼮��̽���ͷ���������������������䲻���ˡ�
��������һ����ʵ��ѧ��д������˵���������ƽ����µij嶯����ʹ�����ఴ�䱾������Ŀ��Ȼ���֣���һ���ܴ�Ŀ��顣
����Ԭ ����������д�Ȿ������ѵĿ��飬Ҳ���Ҹ���������Ŭ���ĵط�����Ȼ�Ҳ���˵�Լ��Ѿ����ĺܺã���������������������ʶ�ؿ��ƽ����µij嶯�������ܵذ���ʷ����ı�����Ŀȥ���֡��Ҳ�֪�����Ƿ�ע���Ѱ���ࡷ��һ�½ڵĽ�β���������β��ǣ�Ӧ��˵�������β�����������������֤���������Ȥ���������������һ������һ����ʵ��ѧ������˵��Ҫ������������ʵ������IJ����ס�
������Сƽ��д���˵���ʷ����������һ���ɻ���д�µ������ʷ�����ڸ��㷺����Ⱥ��˵�кμ�ֵ�����Ƿ��й������Ŀ�����������ô��ģ�
����Ԭ������Ȼ��д����ʷ����С�ĸ��˵���ʷ����ʷѧ���Ǻ�����µ���ʷ��ȣ���д��һ�п�����������������ţ�����ʷ������ǰ���������еĸ����ܴӲ�ͬ�Ķ��ؽǶȻ�����ʷ���ھ���ʷ����¼��ʷ������ij�̶ֳ���Ҳ�����ʷ���ֲ���ʷ����������µı߽ǿհס��������ڿ����Ĺ�������ʷ���������Ļ����������ʷ����������ƺ��������ˣ����ڱ��ˣ���ͨ�˲����κ�Ŀ�ĵļ���������ֲ���Щ���ڣ����ǹ�ͬ������������Ϊ�ָ���ʷ�������ò�ṩ����ʷ�ϼ�ֵ�ı�ī��
����Ҳ������Ϊ��ʼ�����ѵ���ʶ���Լ�����д��ʷ�������ǽ����£�������Ҫ���Լ������ܳ��ֿ���������ǰ��˵�ġ����ƺ����ԡ� ���ܾ������ֿ�����ʹȻ���Ҳ�ϣ����̫����ѧɫ�ʵĶ������ǿ��ܻ�ʹ�˲������塣�������˳����ڡ��ջ��Ϸ��ĵ�һƪ���¡�����������1976��Ϊ��ѹ�����ɡ�������̫Ũ���ˣ�һ�����кܶණ��û�л��߲���д���������������ң����·���ʱ�Dz�������ɾ�ڣ�Ϊʲô���Ƕ����ؼ�ʱ�̾��Ȼ��ֹ�����кܶ�δ��֮�ԣ����룬����ܾ�����˵�ġ���ס����������������Ҳ����һ�����ڴ�ס�ĵط�ͣ���Ķ��ĽŲ�˼��һ�£��ҵ�Ŀ�ľʹﵽ�ˡ�
������Сƽ���ܶ����ĸ��˼��䣬������ָ�����ԭ����ʧ�ˣ������������ԡ������û����ļ�¼��Ҳ�ս���ʧһ���������ر�������������ֽ��ȸУ���������������ڴ��ݵģ����ܿɹ���ǣ���Ϊ������֮һ�����߽������ʷ��ͬʱ���������������۶����ԵĴ�����
����Ԭ�������֡��ֻš����治��˵˵�ģ��㿴��û���κ����ף��������е���Ҳ��û��һ��˼���������ж�ȴͻȻ��˵�߾����ˡ�����ĺܺ����δ���ǰ��Ϊ���Ϻ��������й������ر����������º�����ڼ��й����ˡ�������δ���ǰû��������һ��ȥ�������ж�����������û������һ�仰���Ҵҵ��뿪��������硣��˵����������Լ�����ڴ���ǰȥ�����������������ˣ�˵ס���Ƕ�ҽԺ�ˣ���Ҷ���֪���Ƕ�ҽԺ����������м������������б���£���˵���Ǿ͵Ƚں������ҽԺ��ַ��ȥ�����ɡ������룬��һ����������������������ĺܴ�������˵��ô�ܲ��ֻ��أ����г��������ٰ���飬��Ҳ������һЩ�������ٲɷ����ж�����������û�п����ˡ�
����û��Ҫ�ø���
�������е���ʷ�Ĵ�ʹ
������Сƽ�����ط�1976��Χ�ơ��������ԡ���չ�������˿���롢�����������������������ʹ������д�Ĺ��̳�ӯ��һ�ֽ���ʽ�Ķ����������ж���̽���µĸо���
����Ԭ������˵���ж���̽���µĸо���������Ϊ�����ʷ�¼�������������������ţ�����������ֹ����ش��Ҳ�֪����������ڹ������ʮ�����ĵȴ��ͳ�Ĭ����ֻ��ͻȻקס�����ŵ���ͷ��������ؼǵ���һ���Һ������һ��ȥ�������ж������������������緢Ӣ��������ģ�����ٿ������ľ�ɳٶ�ʧ����ȴ��˥�ϣ���һ���Ӿ��ã������ٵ��ˣ���������˳������ͷѰ�����ű�������ࡣ���ڣ��������ж���ͻȻ��������δ��ȫ����յ�����Ҳ�����Ҫʯ�����ˣ�����ĺ��ź���
������Сƽ��������Ϊ�������е���ʵ���������գ����д��ʼ�ս��������������������е����˱�Ǩ��ǰ���ƣ���֮������ԵĶ�Ϥ�۲죬����������Ը������Ͽ��̻���ͦ�ɹ���������α�조�������ԡ������ж�,��������������Ҷ������һ����Ӧ�ǣ����������Ȼ�Ǹ����Ľ������ˣ����Ȿ���д���������ʲô����Ӱ�죿��������ǿ���Լ�д��ÿһ�£����͵�����������ʵ�����ж�������д����Щ������
����Ԭ �����������ЩDZ̨��Ŷ�����뷴��һ�£�������Ȿ���Ժ�������������ж����أ������㲻����Ϊ��д�����ж����ϴ��ڵ�ijЩ�����е����㣬�Ͷ��������˵Ķ�λ�����ʵı仯�ɣ��ҹ�ȥ��һֱ��Ϊ��������Ҳ��Ȼ��Ϊ���ж���������һ�����е�ٮٮ�ߣ����ϸ�������ʮ������ڣ�����һ������������ſ������ǽ����ٻع�ͷȥ�������Ƿ�˳Ӧ�����ģ����������⣬�ڿ���������һ��Ͷ�����˰��ذ�����õġ��������ԡ������ܲ������λ���������ߵ��ǻۺ�����ô����Ȼ���Ҳ���˵Ҳ����Ϊ���ж����Ƿ������˰��Ӣ�ۣ��������ᷨ�ͽ������ֳ���ʷ��ij�ֻ�����
������Сƽ����������д�������ж����ơ��������ԡ����ĵ���������������������ܴ졣����֮�����û�����ڸ����ϵ���һ���ۣ�������û���˸ı�ܶ�����������ġ��������ԡ������������뵽�����һЩ����������ʷ�����д�������������ʣ�С���������ʷ����ײ�����䲻������żȻ�ԣ���ʱ�����������ͻ���
����Ԭ�����ں�����ʷ�����У������С��������˶Ժ�����˵��������ʵ�����ɸУ�����Ѫ�⣬���Ҳ�����������ͻ���
������Сƽ�����ж������Ǹ��ر��ӵ�������¼���������������˵��һ���������˰����ʿ����ͬʱҲ��һ��ȱ��������ų����Ľ����ᵽ�˸������˶�����Ϊ���½⣬����һЩ֪���˶�����ͬ����գ����������Ե���ů�ж���������Ϊ��д���Ƕȿ������������ġ���ȫ�𱸡�����������ж��ʱ�����Ƿ���һ���̶��������˶Դ��¼�������������Ҳ���������е�������
����Ԭ���������˶���ı༭���Ҷ��ôʷdz����⡣��ע���Ļ��������ˡ���ȫ�𱸡�����һ���������������ֵ��ϵĽ����ǣ����˶��¿�����������ȱ����Ӧ�ò��Ǹ�����ʰɣ��˷�ʥ�ͣ����������������Ƕ��˶��»���Ӧ�ÿ��ݴ�ȣ���Ӧ�ÿ�����������?���ܲ�������������Ļ�����Ϊ��ѡ���ˡ���ȫ�𱸡�����һ���ʣ�����ij�̶ֳ���˵���㱾�������ж��������ΪҲ������ͬ����½⣿���룬���Dz�û�а������Ƹ�ʱ����������Ҳû��Ҫ�ø������е���ʷ�����Ĵ�ʹ����һ�����ǰ���ɣ�
������ʵ������
���������У����߳����
������Сƽ�����˽��֮ǰ��д��1976��Ĺ��£���ʱ��д��ǡǡ��С˵��
����Ԭ������ʱ���һ�û������ֱ����һ��ʷ�¼���Ȼ���������������е������Ѿ����Ժ���������ȥ��Ҳ�ǡ��ջ�Ҳ����С�֣��������д���������з����Ĺ��£�С��˵���㶼���ñ���ʲô����ֻҪ�������з����Ĺ���ԭԭ����д��������С˵�������ҽ�1976�귢���Ĺ���д�������������ҵ�һ���ڡ��ջ��Ϸ�������ƪС˵������Ʈ��һ���ơ���
����������ʮ����ǡ��ջ�������С�֣������ü�ʵ������Ϊ����ġ��������ԡ������¼�¼��˵���ﻰ���뵱���С˵��ȣ��Ҹ������Լ�д�µġ��ط�1976���ļ�ʵ���֣�дС˵������Ʈ��һ���ơ�ʱ�Һ���Ʈ�ڿ��У���һ��������������������������д���ط�1976��ʱ�о��Լ��Dz��ڵ��ϣ���̤ʵ�����е������Ҿ�����Щ��ʵ�����ָ����У����߳�������и���˼������ͬʱ��Ҳ���ϣ���ʵ��Ʒ�����ľ��������������˼��������ƫ������ǶȲ�ͬ����������رܣ��ǹ��ɼ�ʵ��ѧ�������Ҳ������������IJ��֣�ȴҲ��д������Ϊ���ѵĵط���
������Сƽ��������Ͽ������齲�������µ�ȷ��С˵�ĺ��زģ�����������������������磬�������ᵽ�����ж����������֮��ĺܶ�������غϣ����й��Ӵ�����������������ҽ��ȴ��¥�����������������е���Щ�����������˷����������Ŀ�̾��
����Ԭ����������������;�е����֣��߽�������ʶ;�����֣���ſ��Զ�����˵������ˡ��Ҵ�������Ϊ������米������������ģ������в��˽�Ķ��������ֶ���������Ϊ���ǿ��������߲��˽����Ͳ������ˡ����ֶ����Ǻ�ÿһ���˵������й����ģ����Dz��ɿ��ܵġ�������һ�����ӣ����dz�����Ưҡ��һֻС�����������������ؼ�����һ��֮�档����һ������������ע��Ҫ����������ÿһ�������ľ�ͷ����һ����į�ķ��㡣
�������յĹ���
������ʵ����������
������Сƽ�����ڡ��������ԡ����������˲���Ը��������ᣬ������һ�¼�Ҳ������Щ�����������������Ĵ���һ�¼����߳�������
����Ԭ�����Ҹ�绹˵��һ�仰�����⻰�Ҳ������˵˵�ģ����ڿ�����˵��ʮ�껹��˵���ˡ�������Ҳ���̫�����Ҹ��˵�⻰�����⣬��������������ط�1976���IJɷú�д���������ҽ�������˸���⻰ȷʵ�������˵˵�ģ���ʷ����û�о������µij�ˢ�ͳ�������Dz�������˵�ġ��������ǡ��������ԡ����ĵ����˿�ʼһ�����������������ǻ��ŵĵ�����Ҳ��������ȥ�������Ӧ�����Ƴ�����������µ�ʱ�䣬��Ϊ���ֻ��ʱ�����֤��һ�С�
������Сƽ������Ҳ�п��ܼ�ʹ�ٹ��ܶ��꣬�ܶ�������Ȼ�������⡣���ȵ��Ǹ�ʱ��һЩ����ȴ����ģ�������ˡ����ο����ȵ�һ�ж���˵������˵���������ʱ���¼������ļ�ֵ�ܿ����ѱ����������ˡ�
����Ԭ����������������С��Ϊ���ط�1976������һ��ר�棬��ӡ������һ�仰�ǣ���˵���ˡ��ط�1976����������ʷ����ǽ����û�д��ƣ�����Ϊ�ش���С��ר�Ÿ���д��һ���ţ���Ŀ�ͽС���ʷ����ǽ��ʱ���ش��ơ�������֮�������������������յ�û�н�����յĹ�����ʵ���������ˣ�Ҳ������˼�ġ�
������Сƽ�����Ƕ�֪����д���˼��䣬��ʵ����д�Ŀ������Լ������ˣ���Ϊ�и����ǣ����Ҳ��Ϊ���̫�������������������дĸ�ף�д��綼д���ر�á�д���IJ��֣���Щ��Ŀ���壬�о����Ѵ��������������еĶ�������������һ��ԭ���Dz�����Ϊдĸ�ף����кܶ��ճ���������л��ر���ʵ��
����Ԭ�����ҳ��ϣ�������������������ҵı���ȷʵ��Щ��Ŀ���塣�����ֲ��岢�����ұ������������Ǹ���������ﱾ�������ʹȻ��д������һ����Ŀ�С����˶�Ա��������˵���������ش��˶����������ػ���١�����Ϊ17��ʱ���ձ�����ץ����Ѻ��ʮ���죻����Ϊ���˿���Ϊ������ʮ����������֤��������һ���Ӵ��Ž������裬һ���ӻ��ڽ��������У������Լ������úܽ������κ����鶼����˼���У�����Խ�׳�һ����Ȼ��������ˣ����������ԡ����������������������ʷ���������������������Լ������˺��Ŀ��ף��������������ġ���Ȼ�ģ�Ҳ����ʵ�ġ�
������Сƽ����Ϊ���������ԡ����������ߣ������衢���綼�������������顣��һ���˵�һ������������Ҫ���¼������Dz�����֮Ϊ������ԭ�㡣�Դ˿������������ԡ����Ƿ�ɿ����������������е�һ����Ҫ�ڵ㣿
����Ԭ����������ô˵�ɡ���1976����ǰ���ҵ�����Ӧ��˵���DZȽ�˳�ģ�û��̫��IJ��ۡ��Ļ��������ʼʱ�һ���Сѧ������ĸ��Ȼ�����ˣ���Ҳ�����ˣ���������������д���ģ��Ҳ�û��̫��Ŀֻţ���Ϊ���ĸ���ڱ��������˺ܶ࣬��ܹ㣬�������һ�����˲���ķ����Ϸ����ȻҲ�����������Ϻ���û�о��ð������ա����ڼ��������ۣ������и���㣬�ܾ������˻����ҡ�Ȼ��1976��Ĵ��죬���ס���硢���ȫ��ͻȻ�䱻ץ���ˣ������������ظе��˾�Ŀ־�Ͳп�Ĵ�ѹ���������ֿ־�ʹ�ѹ���ұ����˼���ů��������˲����£�һ���Ӿ;����Լ������ˣ�Ӧ���е����ˡ�
������Сƽ�����㡰�ط�1976�����ܶ�����������˵ĺܶ���ʷ��Ϣ���������������ɫ�ʵļ�ͥԨԴ�������㸸ĸ���ǹ��������и߲��쵼�ɲ���������������ļ�ͥ������������������������˸о���Щ���࣬�������ϱ༭����������·���dz���һ��ʲô����������
����Ԭ���������������ĺ�1976��ġ��������ԡ����йء��Ҹ��б�ҵ����䵽����֯���������ˡ���������Ҳ��������������ʱ�����ǰ�ҹ������������Ա�ӳ�����ߵġ����顰���˰������ʡ�����ѧ���������Ҫ��ʵ������ѪҺ��(��������ͷ��˵��)�����Ǿ��á��������ԡ����ǡ����˰���ԩ�ٴ������������Ⱥ���֮һ���͵������������ˡ���ʱ��ոջָ��߿�����һ���뿼��ѧ����Ը���������ȥ�������ҵ��ϱ༭˵�����ȵ��������������ǵ�λ����ȥ���顣�����ͬ�����ȥ��һ��û�Ϲ���ѧ��Ҳû������ʲô������Ʒ��С���ˣ�ƾʲô����ʡ����ѧ����ⲻ������ø�ô������־������ڱ༭֮�ʼдС˵����һ����ƪС˵д�ľ��ǡ��������ԡ�������Ĺ��¡���������λ�������ŵ�ԣ����ҵ��й���Э����ѧ��ϰ���༭���۰�ѧϰ�������ֽ��뱱����ѧ�����Ұ�ѧϰ��ͬѧ����������������Һͱ༭����������ѧ���˺ܶණ����Ҳ�Ӵ�������������ѧ�ĵ�·����Сƽ
>�������ž�ѡ��
- ��������ʡ�ڻ������쵼�ƺ����ӡ��ġ�
- ���ຣ��Ůְ�����ڲ��ܼ���Ͷ��ɸ��蹫��һ������
- ���㶫ȡ���ݻ���ҵ���� ��У��ҵ����ҵ����8��ʵʩ
- ���й�����2305��ͧ���8�����й����㵺�캣��Ѳ��
- ���з�����Ĩ���а;������Ƚ��豨��������ʵ��ȥ�˽�
- �������������¼������Ķɽ����� �������ǽ���12��
- �������۰���������δ��20���ӵ��������� 30���ӵ����
- �����ӽ�����������Ƶ�� 6�������Ϸ��ļ�ǿ���






















